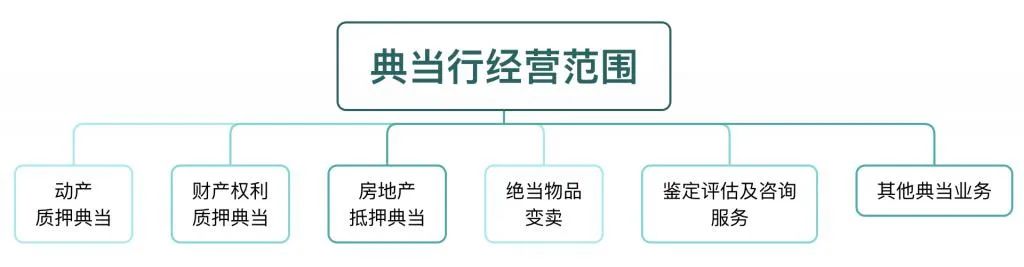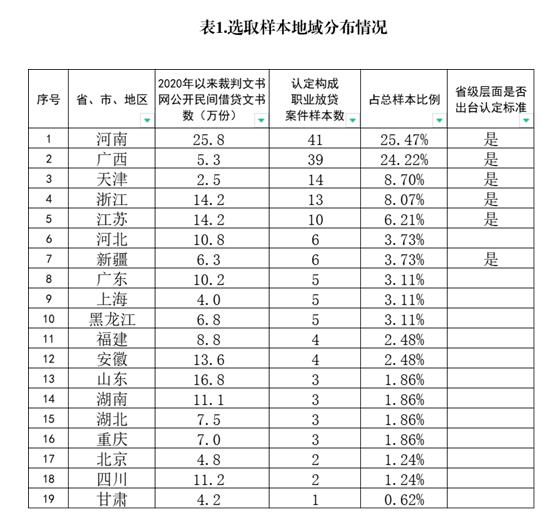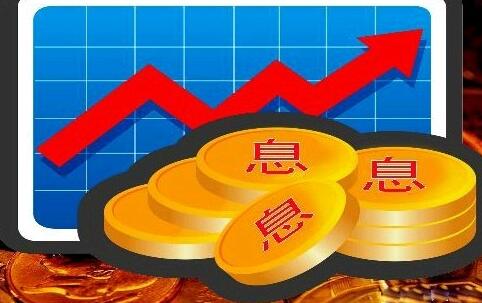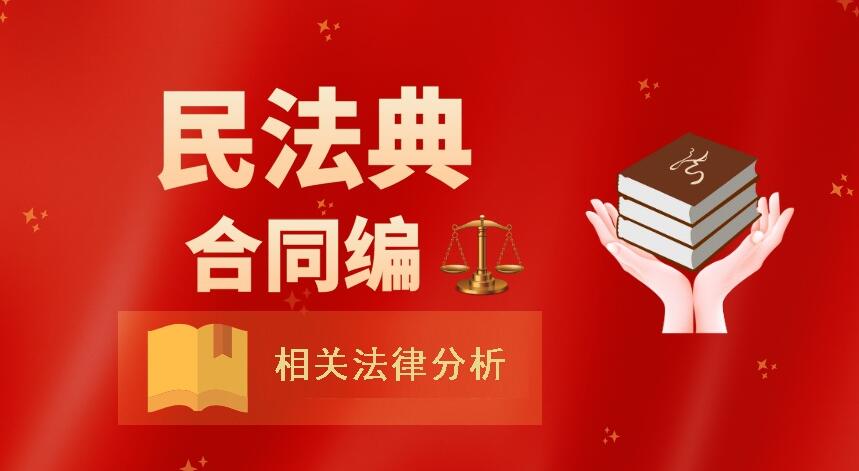论最高额抵押权(二)
发布时间:2015年02月25日浏览量:182来源: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作者:王效贤
三、最高额抵押权的处分
最高额抵押权的处分从广义上讲,包括抵押权次序权的处分与抵押权的处分,前者包括对抵押权次序权的转让与抛弃。[44]狭义上的最高额抵押的处分仅指后者,即对于抵押权的处分,其中又包括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债权的转让以及最高额抵押权本身的转让。我们在此仅从狭义上探讨最高额抵押权的处分。
(一)最高额抵押权的转让
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的转让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尽相同。《德国民法典》第1190条第4项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可以根据关于债权转让的一般规定进行转让。根据上述规定转让债权的,其抵押权并不一并转让。《日本民法典》第398条之七规定:“(一)于原本确定前,自最高额抵押权人处取得债权者,不得就其债权行使最高额抵押权。于原本确定前,为债务人或代债务人进行清偿者,亦同。(二)于原本确定前,有债务承受时,最高额抵押权人,不得就承受人的债务,行使其最高额抵押权。”第398条之十二规定:“(一)于原本确定前,最高额抵押权人经最高额抵押人承诺,可以让与其最高额抵押权。(二)最高额抵押权人,可以将其最高额抵押权分割为两个最高额抵押权,而依前款规定将其中之一让与。于此情形,以其最高额抵押权为标的的权利,就让与的最高额抵押权消灭。(三)进行前款让与,应经以该最高额抵押为标的的权利所有人承诺。”第398条之十三规定:“于原本确定前,经最高额抵押人承诺,最高额抵押权人可以实行最高额抵押权的一部让与,而与受让人共有其最高额抵押权。”可见,在德国是不允许最高额抵押权转让,而日本则允许最高额抵押有限制的转让。
对于最高额抵押权能否转让,学说上也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在最高额抵押权确定之前,抵押权人可以在得到抵押人同意后,将其享有的最高额抵押权转让给第三人。[45]也有学者认为,依担保法规定,抵押权不能与担保的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只能随担保的债权一并转让,而法律又规定最高额抵押权的主债权合同债权不得转让。这样一来,主债权合同债权不得转让,最高额抵押权也就不能转让。[46]即使承认最高额抵押权可以转让的学者,其对于最高额抵押权可否单独转让问题仍存在分歧,很多学者认为,最高额抵押权应当与基础法律关系同时转让。最高额抵押权具有特殊的从属性,不从属于某个具体债权,而是从属于基础法律关系,因此,“最高限额抵押权确定前,仅得与其担保债权所由生之基础关系(该不特定债权即由此一定范围内发生),一并让与。”[47]也有学者认为,最高额抵押权的转让可以单独转让,而不必随着基础法律关系的转让而转让。如日本民法规定,最高额抵押权不但可以单独转让,还分为全部转让、分割转让、部分转让以及共有持份转让几种情况。[48]我们认为,最高额抵押权制度的创设,就是为了鼓励和促进市场交易,提高交易效率,作为一种权利,最高额抵押权人有权在合理条件下对最高额抵押予以处分,将其全部或部分进行转让,这样才能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因此,禁止最高额抵押权转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而且缺乏法理根据,应当允许其在合理的条件下自由转让,满足当事人的经济需求。[49]在此问题上,我国《物权法》采取的做法是积极、务实的。《物权法》第204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最高额抵押是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所有债权作担保,而不是单独对其中的某一个债权作担保,因此,最高额抵押权并不从属于特定债权,而是从属于主合同关系。部分债权转让的,只是使这部分债权脱离了最高额抵押权的担保范围,对最高额抵押权并不发生影响,最高额抵押权还要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对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尚未发生将来可能发生的债权作担保。[50]
正因为最高额抵押权从属于产生它的基础法律关系,其基础法律关系是最高额抵押权存在的前提。因此,在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经确定前,最高额抵押权可以与基础法律关系一并转让,在最高额抵押权人不转让基础法律关系,而只转让某一具体债权时,最高额抵押权不随之转让。但当事人有约定可以转让的,从其约定。根据《物权法》第204条但书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在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前,最高额抵押权随部分债权的转让而转让。当事人的约定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部分债权转让的,抵押权也部分转让,原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额随之相应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转让的抵押权需要重新作抵押登记,原最高额抵押权需要作变更登记。(二)部分债权转让的,全部抵押权随之转让,未转让的部分债权成为无担保债权。[51]在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后,由于此时的最高额抵押权已转化为普通抵押权,应准用普通抵押权的规定,允许最高额抵押权随同其所担保的债权一同转让。
(二)被担保债权的转让
关于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能否转让的问题,《担保法》第61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在当时我国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经济生活出现混乱局面,保障信贷和交易安全,担保法作出上述规定是必要的。[52]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在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债权的转让问题上发生了转变,不再坚持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的规定,而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债权人自己决定,即允许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可以转让。被担保债权既然可以自由转让,那么基于抵押权的从属性原则,最高额抵押权是否也应随之一同转让呢?对此,我国《物权法》第204条作出了明确回应,即“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前所述,抵押权具有从属性,对于普通抵押权来说,抵押权随所担保债权的转让而转让,但对最高额抵押权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最高额抵押权在从属性上具有特殊性,其所担保的并非某个特定的债权,而是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从属于基于基础法律关系而发生的整体债权。因此,在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并不随之转让。正如徐洁博士所指出的,当某个具体债权转让时,只是该债权脱离了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范围,而最高额抵押权并不随着转移于受让人。[53]但是,如果当事人约定当部分债权转让时最高额抵押权也随之转让的,则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意。事实上,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最高额抵押权随着部分债权的让与而转让时,由于转让的部分债权实际上为特定债权,此时的最高额抵押权因其从属于特定债权,使从属性得以复归,开始普通抵押权化,等被担保债权额结算和完成登记后,成为真正的普通抵押权。[54]即,随部分债权(实际上是特定债权)转让的,不再是最高额抵押权,而是普通抵押权化的抵押权,或真正的普通抵押权。[55]在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后,由于最高额抵押权已转化为普通抵押权,抵押权担保债权转让的,基于抵押权的从属性,即使当事人没有约定,抵押权也应随之转让。
四、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
(一)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的意义
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是指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债权,因一定事由的发生,归于具体特定而言。[56]严格地说,最高额抵押权确定应指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债权的确定。由于担保债权确定,使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转化为特定债权,导致最高额抵押权的性质也由此转化为普通抵押权,故学者也将其称为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额抵押权确定,乃基于抵押权的从属性,因所担保债权具体特定后而向普通抵押权转化的事实。
最高额抵押权确定是抵押权制度的重要内容。承认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1.决定优先受偿范围。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在存续期间内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状态而生生不息。在此过程中,某些具体债权会因清偿、抵销等原因而消灭,使其脱离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但一些新的债权可能会随之发生,并被重新列入担保范围,只要不对之进行决算,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就会处在增减变动之中而永不确定。而最高额抵押权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其设立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担保债权的优先清偿。债权终究是要清偿的,要对债权进行清偿,首要的前提就是使债权得以具体特定。否则,将会使所担保的债权一直保持流动性而无法清偿。谢在全先生认为,最高额抵押权的优先受偿虽然有最高限额的限制,但是计算担保债权的金额是否逾越最高限额或实际债权额究竟有多少,也需要将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加以具体化、特定化。[57]因此仅有最高限额的限制并不足以使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特定化,要使此处在流动中生息不已的债权得以确定,还必须由当事人事先约定或由法律直接规定一特定的日期,一旦该日期届至,最高额抵押权的流动性即应归于终止,只有在该日期以前发生且未逾越最高限额的债权才能纳入最高额抵押权优先受偿的范围。
[NextPage]
2.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最高额抵押权确定制度一方面决定着最高额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保护着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最高额抵押权人在担保债权确定之前,其债权数额增减不定,将来所发生的债权总额无法预测,同一抵押物上的顺序在后的抵押权人、抵押物所有人以及一般债权人的权益均处于不安定状态,因债权尚未确定,无法通过清偿等方法消灭该最高额抵押权。[58]由此则使最高额范围内的担保债权一直处在受拘束状态,对于抵押物的剩余价值也无法予以利用,严重限制了抵押物交换价值的充分发挥。因而法律有必要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使最高额抵押权归于确定,对确定的最高额抵押权可因清偿现存的被担保债权额而使之消灭,并且可以与其他一些制度,如日本民法上的消灭请求权及减额请求权制度互相配合,从而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59]从这一角度来说,最高额抵押权确定制度确有使抵押物所有人摆脱最高额抵押权的束缚,使利害关系人的地位稳定的作用,称其为一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制度当之无愧。
(二)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的效力
最高额抵押权一经确定,担保物权的流动性即被终止,由于所担保的债权已被固定,其便由原来的不特定债权转化为特定债权,最高额抵押权的性质也将发生相应的变更,从而具备了普通抵押权的一般特性。一般认为,最高额抵押权确定后,将发生如下效力。
1.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确定。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相当于为债权划定了分界线,确定之前已经存在尚未消灭的债权,其在最高限额以内的部分为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范围,超出最高限额的部分则沦为一般债权,非为最高额抵押权的效力之所及,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确定之后发生的债权,即使其产生于原基础法律关系也不属于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不为抵押权的效力所及。但需要注意的是,确定时存在的债权原本不限于已届清偿期的债权,其他未届清偿期的债权或附有条件的将来债权,也包括在内。[60]确定后的抵押权在形态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再是担保整个不特定债权的最高额抵押权,而表现为担保数个确定债权的普通抵押权。此时被担保的债权总额会因债务人对其中部分特定债权的清偿而减少,使原本已列入最高额抵押权担保范围的债权因清偿而消灭,从而使担保债权总额达不到最高限额。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债权确定后依原来的基础关系新发生的债权,也不能再计入最高限额,对此徐洁博士称之为“最高额抵押权确定之后,债权只能‘出’,不能‘进’被担保债权范围。”[61]
2.主债权确定后利息及违约金等的处理。普通抵押权的担保范围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抵押财产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在抵押权实行之前,虽然主债权数额是固定的,但是利息等却在不断增加,具有流动性,这些增加的利息等费用依然属于被担保债权的范围。同样,最高额抵押权在确定后,其性质已经普通抵押权化,亦应按照普通抵押权的实行规则处理,即确定时已存在的被担保债权,其利息、迟延利息和违约金等如果在确定时已经发生,如果与主债权合计没有超过最高限额时,可以记入被担保债权;即使在确定之后发生,如未超过最高限额,仍可记入被担保债权;甚至确定时存在的部分主债权因清偿等原因而消灭,致最高限额未达满额时,其他主债权所生的利息等,仍可继续计入被担保债权以填补空额。[62]由此可见,被担保债权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无论在确定时是否已经发生,均属于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确定后新生利息之所以能够成为被担保债权,是因为这类债权发生的原因事实在最高额抵押权确定时已经存在,属于已特定但未发生的债权,而此类债权属于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范围。[63]
3.最高额抵押权从属性的转化。在最高额抵押权确定之前,由于所担保的债权范围没有确定,最高额抵押权并不从属于各个已经存在的具体债权,而是从属于产生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确定之后,最高额抵押权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即转化为普通抵押权,其从属性也和普通抵押权一样,不再具有特殊性,而是从属于已经确定的具体债权。有的学者称此为抵押权从属性的复归,[64]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所谓复归是指回复到某种状态,抵押权从属性复归意味着该从属性一度消失而再度出现,而我们认为最高额抵押权的从属性从未消失过,只不过是随主债权的确定而发生了变化,称之为“从属性的转化”可能更确切些。在最高额抵押权确定之前,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不仅可以改变债权的最高限额和决算期,甚至改变发生债权的基础法律关系,而且可以将最高额抵押权单独或部分转让。但在确定之后,由于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不再变化,上述事项也不能任由双方当事人改变,此时的抵押权如若转让只能与所担保债权一同转让。
(三)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的事由
最高额抵押权既可以基于双方或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确定,也可以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而确定,对此世界各国立法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事由。
1.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1)因约定的决算期届至而确定。决算期是指确定最高额抵押所担保债权实际数额的日期,根据各国立法例和学说,决算期是指用来将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予以特定化的时间,其法律性质为期日。在我国《物权法》中决算期称为债权确定期间,实践中,最高额抵押权人为了防止抵押人任意行使确定债权额的请求权,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抵押人为了防止自己的抵押物所担保的债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般都愿意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对债权确定的期间进行约定。[65]所以,对决算期进行约定是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重要内容。如果最高额抵押当事人预先约定了决算期,则在决算期届至时,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额即自行确定。最高额抵押权之所以设有决算期制度,除为满足确定最高额抵押权的需要外,还具有排除抵押物所有人行使确定请求权的效力。[66]在约定的决算期届满之前,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抵押物所有人不得单方请求确认债权,从而给抵押权人、债务人一个合理预期,免除其对抵押物所有人行使确定请求权的顾虑。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债权确定的具体日期,只是约定了实现最高额抵押权的特定事由,此时债权也必须确定。因为根据《物权法》第203条的相关规定:“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而最高额抵押权人行使最高额抵押权的基础就是担保债权额的确定,所以出现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最高额抵押权的事由就意味着担保债权额的确定。[67]
(2)因双方合意终止抵押权而确定。最高额抵押权是由双方当事人合意设定的,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既然可以协商设定最高额抵押权,当然也有权合意终止抵押权。当双方当事人合意终止最高额抵押权时,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因此确定。即抵押合同中未约定决算期的,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经协商一致,随时进行抵押权的决算。[68]在我国台湾地区实务当中,依据由法律行为来定存续期限,当事人有权随时终止其法律关系的法理,承认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均可得随时终止。
(3)因法定期间经过应一方请求而确定。我国《物权法》第206条第(2)项规定:“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起满二年后请求确定债权”。根据上述规定,抵押当事人对债权决算期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均有权自法定二年期间届满后请求确定债权,当一方当事人提出债权确定请求时,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确定。《物权法》这样规定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设立最高额抵押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连续性的交易提供担保,连续性交易一般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允许当事人随时要求确定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额,就意味着一方当事人,特别是抵押人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要求确定债权额,这无疑与设立最高额抵押权的目的不相符合;二是在当事人对确定债权额的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清楚的情况下,规定一个法定的确定债权额的期间,可以使最高额抵押权的地位因法定期间的存在而较为安稳,抵押权人不必时时顾虑抵押人行使确定请求权。这对于稳定最高额抵押关系是有好处的。[69]从《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使请求权的主体包括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但从上述解释来看,该条规定的目的显然侧重于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避免因抵押人随时提出债权确定请求,影响最高额抵押关系的稳定。对《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70]:①二年期间的起算点为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以抵押物性质不同有所区别:对于建筑物、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不动产权益抵押的,最高额抵押权的设立之日为最高额抵押权登记之日;对于以交通运输工具等动产抵押的,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生效之日。②二年是一个固定期间,不可改变,也不存在中止、中断的问题。③抵押人及抵押权人均可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二年后请求确定债权。④此项权利是法律赋予双方当事人的,不允许当事人之间以约定方式加以排除,有排除约定的,约定无效。
[NextPage]
2.基于法定事由的发生
(1)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是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在新的债权没有继续发生可能的情况下,则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额也确定。因此,我国《物权法》第206条第(3)项将“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作为债权确定的事由之一。《日本民法典》第398条之二十第1款第1项亦曾规定:“因应担保债权范围的变更、交易终止或其他事由,应担保原本不再产生时,最高额抵押权应担保的原本予以确定。”[71]谢在全先生认为:“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者系抵押权人与债务人间签订之特定经销契约所生之债权,而该经销契约已因期间届满而当然终止,此际抵押权人对债务人已无继续发生债权之可能,是该最高限额抵押权自应归于确定。”[72]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继续性交易的终止。如果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是基于继续性交易而产生的,则该继续性交易终止时,该债权已丧失发生的可能性,最高额抵押权即应确定。如果继续性交易关系解除的,亦发生同样的后果。二是基础法律关系消灭。最高额抵押权是为了基于基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连续性不特定债权提供担保,当基础法律关系因终止、解除等原因而消灭时,其担保债权无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最高额抵押权从而确定。[73]
(2)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我国《物权法》第206条第(4)项将“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作为债权确定的事由之一,理由在于:“在最高额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财产被法院查封、扣押的,其有可能被拍卖或者变卖。抵押财产被拍卖、变卖的价格直接影响到最高额抵押权人债权利益的实现,为确保自己的利益,在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时,最高额抵押权人一般都希望被担保的债权尽早确定。此外,查封、扣押抵押财产实际上隔断了抵押财产与担保债权的关系,也脱离了最高额抵押人和最高额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的影响和控制,因此,无论是从保护最高额抵押权人、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角度,还是从稳定担保关系的角度,都应当确定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额。”[74]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抵押物不论是依执行申请被查封,还是依财产保全被查封,并不构成最高额抵押权当然确定的法定事由,并不必然导致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因为,抵押物被查封、扣押,并不必然导致抵押物被强制拍卖,只是在其权利上被强行设定了一定限制,抵押人或债务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提供其他担保以申请解除该查封、扣押。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根据约定,办理了登记的担保物权应当有效,只是基于此限制,抵押权人在此之后发生的债权的担保效力不得对抗财产保全申请人。一旦抵押物被解除查封、扣押,该限制解除,则该部分债权的担保限制解除,担保效力回复圆满,得对抗第三人。如果因抵押物被查封、扣押,就当然导致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则在抵押物被解除查封、扣押后,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不可能再继续依据该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发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结果并非当事人所期望,显然不符合市场需求。[75]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但并不意味着抵押财产就一定会被强制执行,当抵押人或债务人通过清偿或提供其他担保方式申请法院解除了对抵押财产的查封、扣押时,只要双方约定的决算期尚未届至,双方的担保关系仍可继续进行,显然此时要求债权确定是不必要的,这样不仅会损害债务人和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利益,而且也不利于交易的进行,从而影响市场的效率。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民法”第881条之十二第6项“但抵押物之查封经撤销时,不在此限”的规定,对最高额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在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限制,使得最高额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后产生的债权的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查封、扣押的申请人,然而一旦撤销查封、扣押,那么最高额抵押权回复到原来的状态。[76]当然,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之后被强制拍卖的,则最高额抵押权即被确定。
(3)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在最高额抵押权存续期间,债务人、抵押人有可能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所产生的直接法律后果就是债务人、抵押人进入破产程序或者清算程序。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破产申请受理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可以由担保物获得清偿。而最高额抵押权只有在确定后,才能就抵押物实现抵押权。因此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使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确定成为必要。同理,在债务人、抵押人被撤销的情况下,债务人或者抵押人进入清算程序也需要确定担保债权额。
对于以上几种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的事由,我国《物权法》第206条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此外在第206条第(6)项还设计了一个兜底条款,即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这是为了适应实务的发展需要作出的概括性规定,如有些学者列举了债务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等,即使约定了决算期,债务人出现上述情形的,抵押人也可以依情势变更原则行使确定请求权,使抵押担保的债权予以确定。[77]
【作者简介】
王效贤,单位为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注释】
[1]王利明:《物权法论》(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640页。
[2]黄任章:《论最高额抵押》,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5期。
[3]谈婧:《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华东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
[4]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页。
[5]何志:《担保法审判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6]房绍坤、郝倩:《最高额抵押权法律特征剖析》,载《政法论丛》1997年第6期,第5页。
[7]房绍坤、郝倩:《最高额抵押权法律特征剖析》,载《政法论丛》1997年第6期,第5页。
[8]郭明瑞:《担保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9]黄任章:《论最高额抵押》,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5期。
[10]傅穹、彦明:《再谈最高额抵押》,载《法律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1期。
[11]刘晨:《论最高额抵押制度》,复旦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9页。
[12]欧琴:《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完善》,重庆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13]许明月:《抵押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14]胡大展:《最高额抵押的法律沿革和特征》,载《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的2期。转引自谈婧:《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华东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15]日大审院明治34年10月25日判决,民录第7辑第9卷,第137页,转引自许明月:《抵押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16]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二)》,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155页。
[17]参见刘晨:《论最高额抵押制度》,复旦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18]谈婧:《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华东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24页。
[19]付子堂:《法理学进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20]欧琴:《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完善》,重庆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NextPage]
[21]房绍坤、吴兆祥:《论最高额抵押权》,摘自中国民商法律网。
[22]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页。
[23]第三卷,第181页。转引自谈婧:《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华东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24]参见房绍坤、吴兆祥:《论最高额抵押权》,摘自中国民商法律网;另参见谈婧:《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华东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25]房绍坤、吴兆祥:《论最高额抵押权》,摘自中国民商法律网。
[26]黄良友、钟乾刚:《试论最高额抵押》,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4期。
[27]徐武生:《担保法理论与实践》,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28]欧琴:《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完善》,重庆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29]陈祥健主编:《担保物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30]张鑫伟:《浅析最高额抵押权的设定》,载《法制与经济》2010年2月总第230期,第55页。
[31]许明月:《抵押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
[32]谈婧:《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的最高额抵押制度》,华东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0页。
[33]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711页。
[34]许明月:《抵押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
[35]邓曾甲:《日本民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36]欧琴:《论最高额抵押--兼论我国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完善》,重庆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刘晨:《论最高额抵押制度》,复旦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
[37]许明月:《抵押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38]参见谢在全:《最高限额抵押权变更之研究--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评释》,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
[39]参见谢在全:《最高限额抵押权变更之研究--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评释》,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
[40]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修订第1版,第331页。
[41]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
[42]房绍坤、吴兆祥:《论最高额抵押权》,载《法学家》1998年第2期。
[43]参见程啸:《中国抵押权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457页。
[44]参见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71页。
[45]参见徐洁:《抵押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46]郭明瑞、杨立新:《担保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47]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页。
[48]参见刘晨:《论最高额抵押制度》,复旦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49]吴春林:《最高额抵押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页。
[50]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页。
[51]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页。
[52]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页。
[53]参见徐洁:《抵押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54]张燕燕:《我国最高额抵押担保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
[55]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页。
[56]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9页。
[57]参见谢在全:《最高限额抵押权确定之研究--台湾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评释》,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
[58]徐洁:《抵押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59]参见高圣平:《物权法担保物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310页。
[60]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4页。
[61]徐洁:《抵押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63]岳德山:《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研究》,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3-14页。
[64]参见张燕燕:《我国最高额抵押担保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65]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446页。
[67]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9页。
[68]参见叶金强:《担保法原理》,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69]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447页。
[70]参见王旭光、范明志:《物权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页。
[71]由于该规定所列举的确定事由特别是其中的“交易终止”在内涵上模糊不清,使得最高额抵押当事人的地位极不安定,且该规定也不利于最高额抵押的流转,故2003年日本修订民法典时,删除了这一规定。参见孙鹏、王勤劳:《最高额抵押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9月总第106期,第90页。
[72]谢在全:《最高限额抵押权确定之研究--台湾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评释》,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
[73]参见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4页。
[74]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7-448页。
[75]吴春林:《最高额抵押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3页。
[76]参见李雷红:《最高额抵押权担保债权确定研究》,烟台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77]参见吴春林:《最高额抵押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3页。
温馨提示:如需业务、风险在线讨论,辽宁省内典当企业请加入辽宁省典当协会会员群(133649286),外省典当企业可加入典当精英群(52233943),加入时请注明典当行全称与真实姓名。



 典当新闻
典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