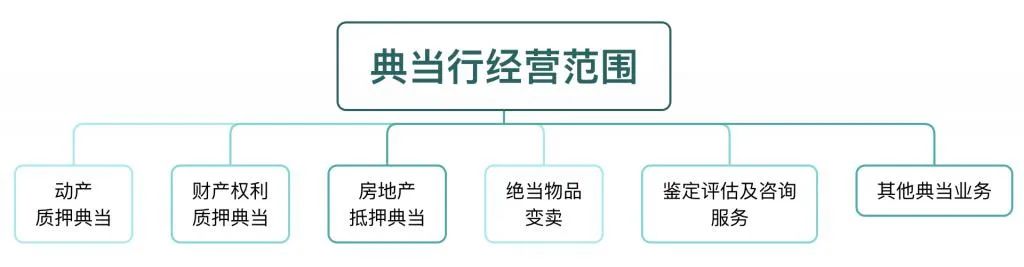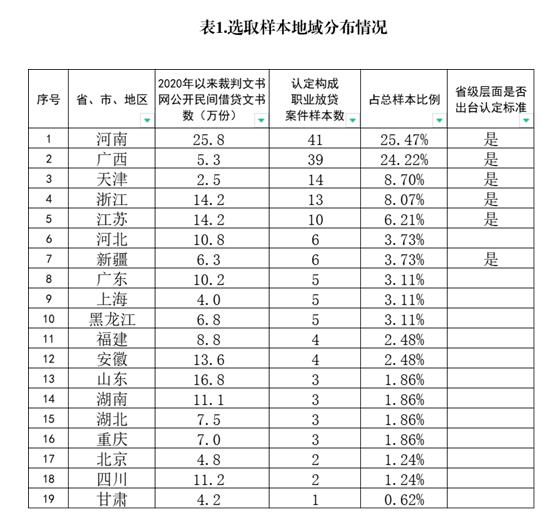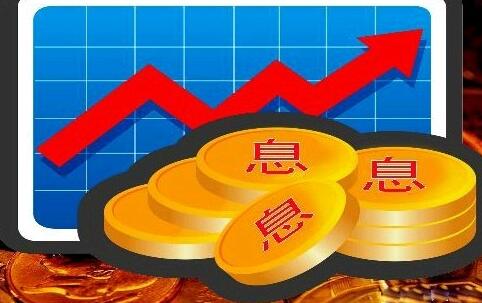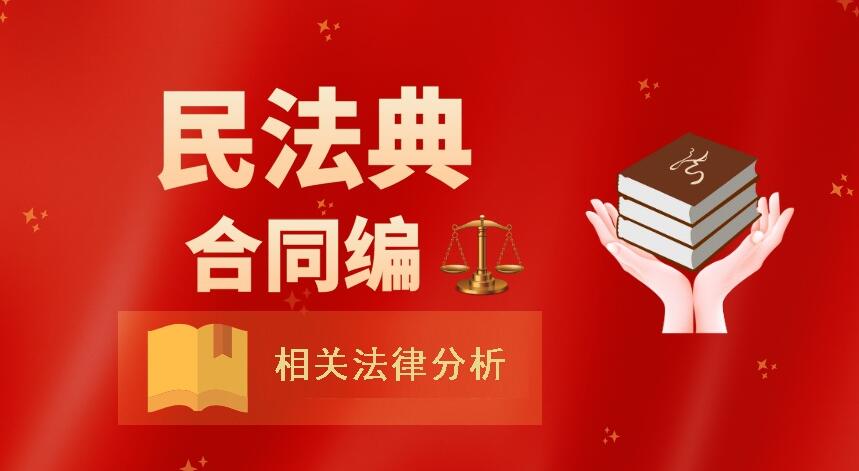如何确定司法查封后最高额抵押权优先受偿的范围
发布时间:2014年01月15日浏览量:130来源:辽宁典当网作者:谢裕宽
案件回放:A外资公司来中国购地建房设厂,B公司与A公司有业务往来,A公司拖欠B公司款项1500多万元,于是B公司只好起诉A外资公司,并向法院申请了诉讼保全,要求法院查封A外资公司的银行帐户及房地产资产,并向法院提供了A外资公司的银行帐户信息及土地信息。法院受理后立刻对其进行了查封。之后,因为A公司有大笔外汇入账,故要求调解,先行偿还500万元,其余1000万元分期归还。B公司认为:因为A公司的土地除去银行贷款以后的价值预估不低于八、九百万,只要土地不解封,按照该方案操作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的好办法。所以在法院的主持下,该案调解结案,B公司解封A公司帐户的同时,A公司支付500万元给B公司,A公司分期偿还B公司1000万元,A公司土地继续查封。
似乎这个案子比较圆满的解决了,但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当分期履行的期限届满,A公司并未支付任何钱款,而且相关外方人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奈之下B公司果断申请法院执行,要求强制执行A公司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偿还其工程欠款。但更让人吃惊的是法院告知B公司,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处置收益全部归C银行所有。
原来A公司与C银行之间设立了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当法院去查封A公司土地之时,以该土地为抵押物的最高额抵押贷款中还有最后两笔贷款未发放,但是当法院去执行之时,最后的贷款已经发放完毕,C银行已经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最高额全额放贷给了A公司。
问题就来了,难道抵押物查封以后银行还可以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给A公司放贷并全额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吗?
我们暂且搁置一下这个问题,案情还在继续。之后,C银行向法院起诉A外资公司,要求对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主张优先权,B公司自然对此不服,立即向法院申请,要求追加其为第三人。于是对于C银行是否就A公司的全部房地产享有优先权这个问题,C银行和B公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院最终判决是:C银行就全部放贷的债权享有优先权,理由是C银行并不知情法院查封的事实。后该案由B公司向当地人民检察院提起了抗诉,检察院审查后决定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提起重审,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裁定维持原审法院判决,即:C银行仍然就其全部债权享有优先权。B公司无奈,向省最高院提起了申诉,该案现在处于申诉阶段。
我们分析案情即可知道:其实本案中反反复复争论的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法院查封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后,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发生的新债权是否仍然属于该抵押权所担保的范围?且这个担保范围确定的时间节点到底是何时?
对于这个问题现行法律中其实是有规定的,主要是两个地方:
一是《物权法》第206条,该条明确规定,“法院可以查封、扣押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查封以后发生的新债权不再属于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
另一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下称《规定》)第27条,该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起不再增加。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从其知道该事实时起不再增加。”
那本案的情况应该适用那一条呢?这两条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笔者认为根据法律颁布的时间来说,《物权法》颁布在后,《规定》颁布在前,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理应是适用《物权法》第206条。其次,从法律的位阶来说,显然《物权法》相对于最高院的《规定》而言是上位法律,故理应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庭审中,法院认为《物权法》与《规定》不冲突,而且《物权法》第206条规定不够详细的地方,《规定》第27条可以比较详细的解释说明。
这样的解释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法律颁布之前的下位司法解释怎么能够去解释后颁布的上位法律呢?这是有违司法解释的理论和实践的。
其次,《物权法》第206条本身不存在不明确,其干脆利落的表明了观点,即该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的标准并未以查封的人民法院通知抵押人为要件,这是清楚确定的。理应认为法院的查封扣押是自作出时即生效的,因为作为法院这样的国家机构的作为不管是从权利性质来说还是公示效果来说都是高于一般的私权利的。而且该条表述即使不明确,也应该由后颁布的司法解释来详细明确;
再次,该《规定》第27条本身作为司法解释来说就是不合理的。从公平合理角度上来说,作为贷款人的银行在贷款之前本身就有对抵押物相关情况的审查义务,这是所有银行《贷款守则》中的基本原则。《物权法》第206条的本意也是将这种审查义务分配给贷款人,而不是分配给实行司法查封的法院有通知义务,因为由不是利益相关人的法院来承担这种义务本身就欠合理,由其他普通债权人来承担相关不通知或通知不完善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就更为的不公平。
其实,如果我们退一步,从法律适用的纠结中解除出来分析这个案件,我们也可以对此案做出更为深入透彻的分析和法律解读。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本案适用了《规定》第27条,本案的脉络又将如何变化呢?
该《规定》第27条明确:“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受抵押担保的债权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不再增加。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自其知道该事实起不再增加。”
而在诉讼保全之时,审理A外资公司和B公司之间纠纷的人民法院作出了查封A外资公司财产的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明确“查封、冻结A外资公司价值1500万元的存款或者其他财产。”,该裁定书当时是直接送达至送达C银行的,法院在查封A公司名下土地的同时也冻结了A外资公司在C银行的所有帐户,账户余额96.01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恰好因为检察院抗诉,重新审理C银行和A公司抵押权优先受偿纠纷的法院就是这个做出诉讼保全查封裁定的法院。其又在判决中认为:“从裁定书的内容来看,对于抵押物的查封未予以明确,不能视为通知,而且C银行是在法院解封帐户以后进行的放贷,应视为其尽了审慎审查义务。”
笔者认为该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既然《规定》第27条明确了法院应该要履行通知义务,那法院为什么未予以明确通知呢?这是谁的过错呢?难道法院未通知的责任应该有要求诉讼保全的原告来承担吗?法院对于自己依法作出的裁定都不予认可,这是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其实裁定上的表述是一种总括性表示,应该说不但不是不确定,而是相当的确定,就是查封被保全人所有的价值1500万元的财产,有存款的冻结存款,有实物的查封实物,而并没有说明仅冻结存款,这也是法院最普通的通行做法以及诉讼保全的立法原意。所以法院没有理由认为该裁定不能视为是法院对抵押物查封的通知。
其次,而当时A公司是一个只拥有在建厂房并尚未开始营业的企业,除了土地房产没有其他的财产,而该公司的基本帐户就设在C银行,且该公司已经将土地房产都设定了最高额抵押,抵押给了C银行,所以C银行是最了解A公司财产状况的人,法院认为其在解封账号后放贷就应视为尽了审慎义务明显是不正确的。而且根据各银行的《贷款守则》,银行发放贷款之前基本的程序要求中不仅要求银行对借款人的银行帐户有审查义务,更重要的对于借款人、担保人,抵押物等情况进行相应的审查,试问在此情况下C银行如何能不知道A公司的土地厂房被法院查封。作为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如果说这样的情况都自称一无所知的话,那不是C银行自身的失职,就是在撒谎和抵赖。而他的失职不能作为其辩驳和推脱的理由。法院理应认定其知情。
所以,即使根据《规定》第27条的规定,也应认定为法院在向银行送达查封裁定之时即视为送达了抵押物查封的通知,而且根据实际的情况C银行也是对于抵押物的查封是知情的。
从这个案件,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中有些法律事务操作与法条的设立本意是与完全脱节的。我们在这里介绍这个案件,主要目的在于呼吁业界能对此多一点思考、多一点改善。因为如果像本案这种情况都不适用《物权法》第206条,而适用《规定》第27条,并且在适用《规定》第27条时认为本案也不属于贷款银行知情的话,那么必将给企业逃避债务大开绿灯,在社会上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映,因为目前司法实务中,法院在诉讼保全时是不会对该土地的抵押情况进行详细的审查的,从而也不会对查封的相关情况对贷款银行进行明确的通知的,那不通知是不是就都视作贷款银行不知情呢?借款人是不是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继续贷款转移资产,银行岂不因此背负更多的不良资产?那么《物权法》第206条规定岂不成了空文,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当然这个案件给予我们有很多启示,可以在司法实务当中加以注意。人民法院在办理司法查封过程中,如果发现被查封冻结的财产上已经设定了最高额抵押权,是否应当通知最高额抵押权人有关司法查封的情况呢?而律师在代理相关案件时,作为诉讼保全申请人或强制执行申请人的代理人,应当提醒申请人,如果知道被查封冻结的财产上已经设立了最高额抵押权,那么应要求法院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有关司法查封的情况,以避免本案中的纠纷情况,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温馨提示:如需业务、风险在线讨论,辽宁省内典当企业请加入辽宁省典当协会会员群(133649286),外省典当企业可加入典当精英超级群(52233943),加入时请注名典当行全称与真实姓名。
似乎这个案子比较圆满的解决了,但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当分期履行的期限届满,A公司并未支付任何钱款,而且相关外方人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奈之下B公司果断申请法院执行,要求强制执行A公司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偿还其工程欠款。但更让人吃惊的是法院告知B公司,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处置收益全部归C银行所有。
原来A公司与C银行之间设立了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当法院去查封A公司土地之时,以该土地为抵押物的最高额抵押贷款中还有最后两笔贷款未发放,但是当法院去执行之时,最后的贷款已经发放完毕,C银行已经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最高额全额放贷给了A公司。
问题就来了,难道抵押物查封以后银行还可以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给A公司放贷并全额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吗?
我们暂且搁置一下这个问题,案情还在继续。之后,C银行向法院起诉A外资公司,要求对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主张优先权,B公司自然对此不服,立即向法院申请,要求追加其为第三人。于是对于C银行是否就A公司的全部房地产享有优先权这个问题,C银行和B公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院最终判决是:C银行就全部放贷的债权享有优先权,理由是C银行并不知情法院查封的事实。后该案由B公司向当地人民检察院提起了抗诉,检察院审查后决定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提起重审,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裁定维持原审法院判决,即:C银行仍然就其全部债权享有优先权。B公司无奈,向省最高院提起了申诉,该案现在处于申诉阶段。
我们分析案情即可知道:其实本案中反反复复争论的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法院查封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后,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发生的新债权是否仍然属于该抵押权所担保的范围?且这个担保范围确定的时间节点到底是何时?
对于这个问题现行法律中其实是有规定的,主要是两个地方:
一是《物权法》第206条,该条明确规定,“法院可以查封、扣押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查封以后发生的新债权不再属于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
另一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下称《规定》)第27条,该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起不再增加。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从其知道该事实时起不再增加。”
那本案的情况应该适用那一条呢?这两条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笔者认为根据法律颁布的时间来说,《物权法》颁布在后,《规定》颁布在前,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本案理应是适用《物权法》第206条。其次,从法律的位阶来说,显然《物权法》相对于最高院的《规定》而言是上位法律,故理应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庭审中,法院认为《物权法》与《规定》不冲突,而且《物权法》第206条规定不够详细的地方,《规定》第27条可以比较详细的解释说明。
这样的解释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法律颁布之前的下位司法解释怎么能够去解释后颁布的上位法律呢?这是有违司法解释的理论和实践的。
其次,《物权法》第206条本身不存在不明确,其干脆利落的表明了观点,即该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的标准并未以查封的人民法院通知抵押人为要件,这是清楚确定的。理应认为法院的查封扣押是自作出时即生效的,因为作为法院这样的国家机构的作为不管是从权利性质来说还是公示效果来说都是高于一般的私权利的。而且该条表述即使不明确,也应该由后颁布的司法解释来详细明确;
再次,该《规定》第27条本身作为司法解释来说就是不合理的。从公平合理角度上来说,作为贷款人的银行在贷款之前本身就有对抵押物相关情况的审查义务,这是所有银行《贷款守则》中的基本原则。《物权法》第206条的本意也是将这种审查义务分配给贷款人,而不是分配给实行司法查封的法院有通知义务,因为由不是利益相关人的法院来承担这种义务本身就欠合理,由其他普通债权人来承担相关不通知或通知不完善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就更为的不公平。
其实,如果我们退一步,从法律适用的纠结中解除出来分析这个案件,我们也可以对此案做出更为深入透彻的分析和法律解读。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本案适用了《规定》第27条,本案的脉络又将如何变化呢?
该《规定》第27条明确:“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受抵押担保的债权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不再增加。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自其知道该事实起不再增加。”
而在诉讼保全之时,审理A外资公司和B公司之间纠纷的人民法院作出了查封A外资公司财产的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明确“查封、冻结A外资公司价值1500万元的存款或者其他财产。”,该裁定书当时是直接送达至送达C银行的,法院在查封A公司名下土地的同时也冻结了A外资公司在C银行的所有帐户,账户余额96.01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恰好因为检察院抗诉,重新审理C银行和A公司抵押权优先受偿纠纷的法院就是这个做出诉讼保全查封裁定的法院。其又在判决中认为:“从裁定书的内容来看,对于抵押物的查封未予以明确,不能视为通知,而且C银行是在法院解封帐户以后进行的放贷,应视为其尽了审慎审查义务。”
笔者认为该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既然《规定》第27条明确了法院应该要履行通知义务,那法院为什么未予以明确通知呢?这是谁的过错呢?难道法院未通知的责任应该有要求诉讼保全的原告来承担吗?法院对于自己依法作出的裁定都不予认可,这是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其实裁定上的表述是一种总括性表示,应该说不但不是不确定,而是相当的确定,就是查封被保全人所有的价值1500万元的财产,有存款的冻结存款,有实物的查封实物,而并没有说明仅冻结存款,这也是法院最普通的通行做法以及诉讼保全的立法原意。所以法院没有理由认为该裁定不能视为是法院对抵押物查封的通知。
其次,而当时A公司是一个只拥有在建厂房并尚未开始营业的企业,除了土地房产没有其他的财产,而该公司的基本帐户就设在C银行,且该公司已经将土地房产都设定了最高额抵押,抵押给了C银行,所以C银行是最了解A公司财产状况的人,法院认为其在解封账号后放贷就应视为尽了审慎义务明显是不正确的。而且根据各银行的《贷款守则》,银行发放贷款之前基本的程序要求中不仅要求银行对借款人的银行帐户有审查义务,更重要的对于借款人、担保人,抵押物等情况进行相应的审查,试问在此情况下C银行如何能不知道A公司的土地厂房被法院查封。作为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如果说这样的情况都自称一无所知的话,那不是C银行自身的失职,就是在撒谎和抵赖。而他的失职不能作为其辩驳和推脱的理由。法院理应认定其知情。
所以,即使根据《规定》第27条的规定,也应认定为法院在向银行送达查封裁定之时即视为送达了抵押物查封的通知,而且根据实际的情况C银行也是对于抵押物的查封是知情的。
从这个案件,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中有些法律事务操作与法条的设立本意是与完全脱节的。我们在这里介绍这个案件,主要目的在于呼吁业界能对此多一点思考、多一点改善。因为如果像本案这种情况都不适用《物权法》第206条,而适用《规定》第27条,并且在适用《规定》第27条时认为本案也不属于贷款银行知情的话,那么必将给企业逃避债务大开绿灯,在社会上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映,因为目前司法实务中,法院在诉讼保全时是不会对该土地的抵押情况进行详细的审查的,从而也不会对查封的相关情况对贷款银行进行明确的通知的,那不通知是不是就都视作贷款银行不知情呢?借款人是不是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继续贷款转移资产,银行岂不因此背负更多的不良资产?那么《物权法》第206条规定岂不成了空文,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
当然这个案件给予我们有很多启示,可以在司法实务当中加以注意。人民法院在办理司法查封过程中,如果发现被查封冻结的财产上已经设定了最高额抵押权,是否应当通知最高额抵押权人有关司法查封的情况呢?而律师在代理相关案件时,作为诉讼保全申请人或强制执行申请人的代理人,应当提醒申请人,如果知道被查封冻结的财产上已经设立了最高额抵押权,那么应要求法院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有关司法查封的情况,以避免本案中的纠纷情况,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温馨提示:如需业务、风险在线讨论,辽宁省内典当企业请加入辽宁省典当协会会员群(133649286),外省典当企业可加入典当精英超级群(52233943),加入时请注名典当行全称与真实姓名。


 典当新闻
典当新闻